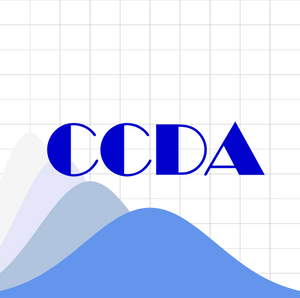北大全球政治风险分析实验室专访唐世平教授:做好中国智库的强大技术支持
一、复旦大学复杂决策分析中心的建设发展探索
Q1:感谢唐老师接受接受我们北大全球风险政治分析实验室的专访。首先请您介绍一下复旦大学复杂决策分析中心的缘起?
唐世平:1999年到2005年我在中国社科院工作,除了写理论文章外还做一些政策分析,也获得了社科院十大杰出青年奖,我现在仍然认为那时候做的很多政策咨询工作还是比较成功的。比如说对2001年“911”后的一些国际局势的判定——“911”事件发生后中文世界的第一篇相关评论就是我写的。我2006年到了新加坡后,开始对政策研究产生了一种距离感。我归根结底还是一个理科生,过去理科的学术训练、跟Robert Powell学习博弈论的经历对我的影响还是挺大的。我当时也想,政策研究不就是靠经验和直觉吗?但问题在于,学者很难拥有多年的政策经验,那些成功的学者型政策分析家的经验是不可复制的。
但实际上,政策研究并不尽然得依靠经验直觉。比如美国的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是做政策研究的,但公司的研究者曾有不少具有数学、博弈论或者统计学背景,比如谢林、布罗迪、冯·诺伊曼等人都在兰德工作过。兰德一直有一个技术驱动的部门、很多研究者具有比较技术化的背景,咱们国家的智库在这方面来说是相对落后的。这是我当初成立复杂决策中心的灵感来源之一。
简言之,我认为中国的智库未能对基于技术性方法的社科研究予以足够重视。譬如我国一些研究者对于俄乌军事冲突的判断,大部分人一开始就认为俄罗斯可以速胜。但是我在去年3月份做过战争推演,认为俄罗斯会打得越来越难,而实际上后来的走向也印证了我的观点。我想通过这个例子说明的问题是,国内很多学者、智库研究者的分析没有模型、数据或推导,只有经验和直觉,我作为一个具有理科背景的学者对这一点不能接受。这就是复杂决策分析中心的缘起之一。
另外一个缘起就是我当时其实已经有打算向计算社会科学这个目标推进政策研究。早在2009年,“计算社会科学”这个词就已经提出,但当时这个概念其实更多强调大数据分析与社科研究的结合。然而,我认为计算社会科学和大数据其实没有必然联系,而计算量才是核心。
Q2:您在创建过程中遇到的困难是什么?又得到了什么样的支持和帮助呢?
唐世平:建立这个决策分析中心我其实花了很长时间,一方面我得找到一些政策研究的方向,另外一个我需要寻找合作伙伴。我自己并不会编程,而从事计算社会科学研究肯定需要编程。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资金支持,这也是中心建立的时候面临的最大困难。为了获得足够的资金支持,你需要说服大家,说明这个中心所从事的研究方向未来可期。在我当时建立中心的时候,咱们国内基本上没有这样的智库,而且当时学过定量的海归人士都很少,所以那个时候国内对这类研究的接受程度是非常低的。
在此 ,我要非常感谢当时支持我们中心建立和发展工作的人,包括张蕴岭老师,王缉思老师,朱成虎将军,崔立如老师,还有黄仁伟老师。虽然不知道我能做出什么成果,他们还是认可我努力的方向。我觉得最大难题就是缺钱,缺钱就是因为没人理解和支持,而这些知名学者当时给予中心最大的帮助,其实是帮我造了势。
Q3:复杂决策分析中心的定位是什么?
唐世平:中心的定位很直截了当,是一个中国战略决策的技术支持机构。我们的目标主要不是写内参,而是发展计算平台、计算技术,用来支持某些决策的计算。你可以认为我们想成为兰德公司技术支持部门那样的机构。当算出一些结果可能对决策有帮助的时候,我们偶尔也会写点内参。
我们中心的定位就是突破核心技术,具体的大规模的实现,可能是用户的工程单位就去解决里边的实现问题。譬如服务器的部署我们不管,我们做的就是最核心的那一块,就核心的算法、模型、架构等等,这个我们做。
Q4:中心秉持什么样的学术理念呢?
唐世平:中心的学术理念其实比较明确,当然就是追求前沿的研究,而不是做诸如社交媒体这些大家觉得耳熟能详的东西。我们想发展新的技术,而且是有一定突破性的技术。不过我们做的一些东西可能不便于公开,除了选举分析预测之外,外界可能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但我们在做技术这个应该是大家都知道的。我们也用很多大家知道的通用技术,比如说机器学习、社会网络分析等,我们想把这些技术组合起来,发展出一个比较重要的有用的技术平台。
Q5:中心的组织方式和运转机制是什么样的?
唐世平:中心组织方式并不复杂。中心不大,老师们来自各个院系的或者是专职人员,真正中心管理者主要就我自己,也有一些其他老师来支持和行政助理负责日常运营。由于我们中心不大,经费也有限,所以我们做的基本上是滚动开发。中心刚成立的时候我们也收到了来自复旦大学和社会人士的一些资金捐助,我把自己长江学者的奖励都投进去了。等中心逐渐运转起来之后,我们就滚动开发,做出了一些成果,用这些成果再去筹措资金,得到一些小额资金来支持我们不断开发新的技术平台。目前,我们也在尝试一些探索性的研究运作机制,基本上是老师、中心技术人员以及学生一起做研究。通常的做法是,由老师提出大致的研究问题、技术方向,然后中心的技术人员可能会具体实施,学生利用业余时间辅助参与。
我们的基本运作机制就是项目制,就是我们有不同的项目、不同的方向。中心的每一个研究者擅长不同技能。有的 Python也很好, R也很好,然后还能做前端,这种是最好的;有的是做算法结构的,有的是可能做算法实现的,那么我们就根据项目来进行不同的人员组合。完成一个项目之后,我们可能就会迁移到另外一个项目上。不过我也不希望它变得特别大,发展到差不多15个到20个人的规模就可以了。
Q6:您是如何建立和管理复杂决策中心团队和保持中心凝聚力的呢?
唐世平:我刚已经提到了,我们中心规模很小,全职研究人员共十多个人,所以现在的管理比较相对简单。全职人员中有七位现在都是老员工了。最重要的是,他们比较认可我们中心想做的东西,因为中心显然不可能像一个公司一样给他们非常好的薪水,他们得喜欢研究本身。

二、复旦复杂决策分析中心主任唐世平老师的学术理念和思考
Q1:创建者的学术理念和抱负一般会给实验室或研究中心这样的机构打下很深的烙印。现在我们想请您谈谈您个人的一些学术经历和思考。如果概括您的学术特色,很多人会用“跨学科”和“全面型”来形容您,您同意吗?
唐世平:我认为我有一个“跨学科”的标签大概是可以的,但是我觉得“全面”是一个不大能够用的词,因为没有人是全面的,我也有很多东西不懂。我可能因为年纪大,比很多年轻晚辈知道的稍微多一些,但总体来说我喜欢跨学科的、有思想碰撞的研究,所以我对自己的阅读面以及自己的关注面都还是比较就是广泛的。简言之,我确实是跨学科,但是也是不全面的,我觉得没有人是全面的。
我之所以从事跨学科式的社会科学研究主要有三点原因。第一,我很关心真实世界的问题,关心中国的命运,关心人的前途或者人的福利。第二,我出身非常贫寒,这对我所关心的问题肯定是有影响的。第三,我的教育背景比较杂乱,因为我自己老是觉得有些东西我可能做不好,或者这一领域做得没什么挑战了,那我就换个领域做。这可能是我性格造成的,我不愿意安于现状,不喜欢总是待在自己的舒适区。
Q2:跨学科研究现在大家都在提,而且似乎只要跨学科就能够创新有所突破。从您的经验来看,您觉得跨学科研究有什么难点或劣势吗?
唐世平:跨学科的挑战性极高,需要阅读不同领域的文章著作、还得将这些知识织成一张网。比如说,写《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的第二章跟考古有关的部分,我花了差不多三年时间才完成,需要阅读横跨人类学、考古学、战争史、国际政治等各类相关领域文献。再如我之前写的“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其创作过程也是很辛苦的,因为它触及到社会科学哲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政治哲学等诸多社科不同领域的内容。
我觉得跨学科还有一个难点在于文章发表的困难。通常来说,跨学科的文章非常难以发表,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论文评审人会是好几个不同学科的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见解。有人会从社会学来说你做的不好,而另一个人会从政治学说你做的不好,这就会让你非常痛苦。因此,在我看来,从事跨学科研究的前提是你先要积累到一定程度才行。而从发表形式来说,著书相较于论文可能更容易呈现出跨学科的研究成果。
Q3:您是否鼓励博士生阶段就开始从事跨学科研究?
唐世平:我一般不鼓励博士生从事跨学科研究,而且也那么没必要,增加劳动的强度和发表难度。博士阶段跨2到3个学科就可以了,不要再跨多了。
Q4:很多社会研究者会特别强调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差异性,而您却在不同场合强调社会科学家都应该读些科学哲学。为什么了解科学哲学对社会科学家具有这样的重要性呢?
唐世平:首先,科学哲学往往建立在对科学史的一些分析上,对于社科学者而言是一种很合适去体会科学的方式,尤其体验到科学突破的那种刹那的但振奋人心的快乐。相比之下,社科研究很难收获这种快乐。科学研究成果的美妙也是社科难以颉颃的,这种美妙社会科学家不容易体会到,也需要通过阅读科学哲学去体会一下。
其次,科学哲学可能会帮助养成批判思维,尤其是反思自己的研究和别人的研究的不足之处。就我个人而言,科学哲学加强了我对机制的理解。比如,你看生物界的所有的物种的适应性都可以用这一个机制来解释,但是它的因素是可以是千奇万化的,这些因素可以是无穷组合,但其根本的普遍选择遗传机制还是一样——你和我的DNA在结构上没有任何区别,这样的东西才是真正的根本性的东西。

Q5:您提到中心的定位是技术,在社会科学中现在技术被等同于定量方法。回到一个长期的定量和定性研究之间的长短之争问题,您怎么看?
唐世平:技术肯定是研究工具,我把它叫打个比方叫医生的手术刀。大家是很清楚的,就这把手术刀能够干什么。但是我们之所以选择这把手术刀,是因为要解决一个特定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不够重要,你用的技术再复杂,我认为它研究本身的意义是相对小的。研究技术是需要用来去干某些特定的事情,我认为在这点上大家已经没有什么太多的分歧了。
讲到研究社会科学的技术,肯定不得不谈定量方法。我认为定量的主要的作用在于甄别对结果有影响的因素,帮助我们验证某种机制产生的结果。然而,你如果要能够甄别机制问题,只能用观察或者是说定性的过程追踪去做,定量其实是没有太帮助的。也就是说定量和定性,它不仅不矛盾,也不应该有争论,因为他们技术上是互补的,是用来干不同的事情的。
定量研究并不等于没有思想或理论深度的研究。现在很多定量研究可能也有很好的思想,也可以有非常深刻的理论,只不过是以定量形式来展现。比如说我比较喜欢的威默(Andreas Wimmer)关于帝国的崩溃和族群冲突的研究,然后罗斯勒(Philip Roessler)的有关非洲族群冲突的研究。我认为他们的理论也是非常复杂了,但是他们是用定量和定性结合回答问题,我认为其问题也足够重要,而且其对问题的回答也是比较令人信服的。
总而言之,我们研究重要的问题,而不能是因为刚好有一套数据去做文章。
Q6:创立复杂决策分析中心、致力于我国智库建设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持,这应该不仅是学术上的追求,还是受到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驱动。请您简单谈谈对学者社会责任的看法。
唐世平:我鼓励我们的社会科学家去关注社会时事,或者成为“公知”(公共知识分子)。我认为公知应该是个正面的词,而不是像现在舆论所认为的一个贬义词。原因很简单,春秋战国时期的孔子、老子、孙子、孟子、商鞅等人都是可以说是公知。而实际上,社会科学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经世致用的科学,所以社会科学家天生的责任就是对社会的现象进行评价、批评和建议。
但除了著书立说之外的与社会进行互动、参与社会辩论才叫承担公知的社会责任。我认为这是每一个社会科学家应该做的。当然不同的人可能在不同的阶段做不同的事情,但是我认为这是我们的职责,其根本性原因在于我们都是社会中的一员,都受社会影响。因此,我们当然有理由也有必要去关心这个社会,因为这个社会本身的变化会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福利都产生影响,我觉得这个是不言自明的。
复旦大学“复杂决策分析中心”简介
复旦大学“复杂决策分析中心”成立于2013年,是我国第一个基于“计算社会科学”,专门为国家战略决策提供技术支持的研究中心。中心立足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和问题前沿,直面变化与复杂的世界,旨在建立起一套基于广泛而丰富的历史经验和科学方法的分析框架、模型和工作软件,将前沿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与实际的学术和政策研究结合起来;把战略行为和战略决策研究的经验一般化、模型化,做到可复制、可移植。通过改进或整合既有的技术平台,开发新的技术平台,成为国家战略决策的技术支持中心,为我国的战略分析和决策提供技术支持。
中心的成立得到了来自国家多个重要部门和机构的支持。从2016年起,完全抛开民意调查,而是基于计算机模拟仿真技术,中心的团队已经连续五次精准预测了美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选举结果。中心还开发了多款针对其它复杂决策问题的计算模拟预测平台。
唐世平教授简介
复旦大学“复杂决策分析中心”主任为唐世平教授。唐世平教授是复旦大学特聘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作为当代中国最具国际影响的社会科学家之一,他在多个领域均有广泛丰硕的成果。迄今为止,他已出版英文专著五部、三部中文专著、一部英文编著和三部中文编著。其中,Social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牛津大学出版社,2013年)于2015年荣获国际研究协会(ISA)“年度最佳著作奖”,是亚洲和中国首位获此殊荣的学者。他的第五部英文专著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经济发展的制度基础)于2022年在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他也是多个国际顶级和一流刊物的第一位来自中国的编委会成员。
唐世平教授是中国计算社会科学,特别是决策计算的拓荒者之一。他提出了基于“全数据计算”(total data computation) 的“决策计算社会科学”理念。